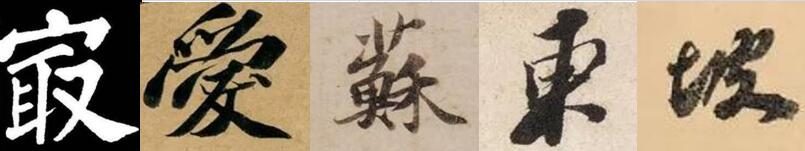苏轼诗中的第一位“低”僧
天下名山僧占多,苏轼酷爱游山玩水,免不得就会结交和尚道人。
交往的化外之人虽多,但真正能让他心有戚戚写入诗中的绝少。留下名字的,自然就更少了,佛印和参寥是当中的佼佼者。
但我今天却不讲高僧,专讲低僧。
有人要笑了,世上虽有俗人雅人,圣人烂人,却第一次听到低僧一词啊。
低僧你可以认为是我的生造,但我也实在想不出另外的词来形容这家伙了。
不卖关子了,我们且看《自普照游二庵》里怎么写的:
长松吟风晚雨细,东庵半掩西庵闭。
山行尽日不逢人,裛裛野梅香人袂。
居僧笑我恋清景,自厌山深出无计。
我虽爱山亦自笑,独往神伤后难继。
不如西湖饮美酒,红可碧桃香覆髻。
作诗寄谢采薇翁,本不避人那避世?
第三句里的居僧,显然就是普照僧的一个和尚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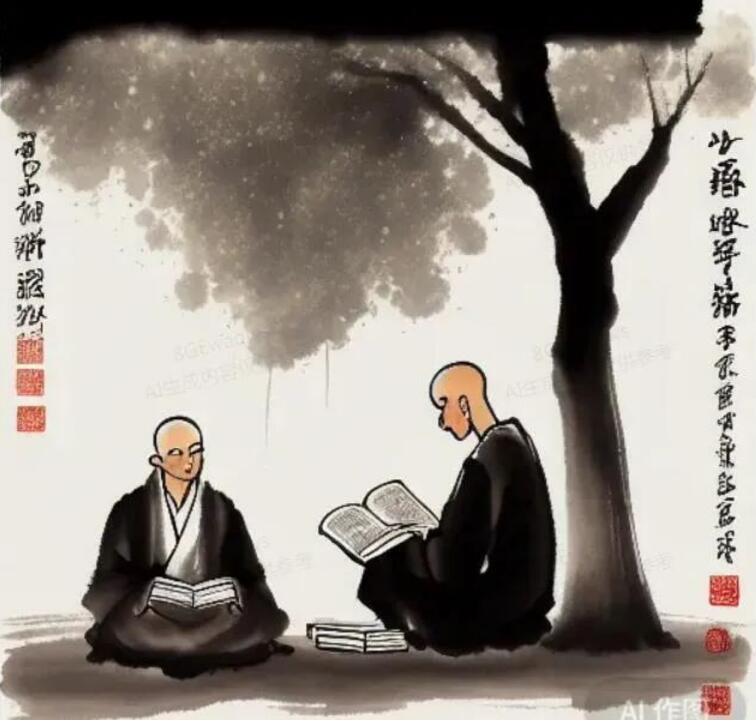
普照寺可不简单,具体的我也不去找了,就以本诗前一首《独游富阳普照寺》里的句子做解吧:
富人真古邑,此寺亦唐余。
鹤老依乔木,龙归护赐书。
从中可知,普照寺是乃唐朝所建。就算历史只有几百年,在古刹里算不得悠久,但架不住人家有名啊,连皇帝都给他们赐过书呢。
大伙应该晓得,虽然僧尼道友常讲四大皆空,但寺庙从来并不超然的存在,有一道御书、有一块金匾,不但是他们的传家宝,更是至少在一朝一代能够存续发展的重要保证。
可就在这所寺庙里,却有和尚笑呵呵地揶揄苏轼:
老兄啊,这山这庙这风景,是你的诗和远方,却是我想要逃离却逃不掉的苟且啊。
前面我们说,能在苏轼诗中留下一鳞半爪的,至少是高僧以上,但这位哥们明显是以极为接地气的坦诚,获得了苏轼的尊重。
用现在的话说:
不装逼,我喜欢!